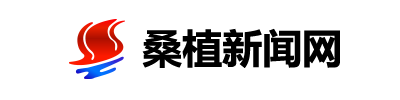
桑植融媒6月30日讯(通讯员 谢德才)车子向着桑植县龙潭坪镇深处而去。窗外,夏日晴空蓝得晃眼,山峦叠嶂,绿意汹涌。此行随镇里的几位干部下乡,目的地是银市坪村——去探访一棵盘踞村头的古楠树。
车近银市坪,确乎有好大一个坪。青翠的山峦,如巨臂环抱,将一片坦荡沃土稳稳托在掌心。公路如带,依山而过。视野开阔得令人心气一舒。这山围绿野的格局,前方田埂小路上,一位扛锄的汉子见车来,停下脚步。他身形敦实,面色是土地染就的赤铜。乡干部摇下车窗,招呼。他咧嘴一笑,露出与土地一样朴实的牙齿:“看老楠树,跟我来!”

这汉子姓魏,是这村里的人。他引着我们踏上一条被脚板磨得光滑的土径,不过百余步,那棵古楠便撞入眼帘。不必谁指点,它自身的存在就是宣告。粗壮的树干,拔地擎天,深褐的树皮沟壑纵横,镌刻风霜雨雪的印记。五个人手拉手,方能勉强合围。它静默地立着,庞大的根系,却如潜行的巨龙,在泥土之下,沉稳有力地延伸、抓握,支撑这庞然之躯,也仿佛紧攥这片土地深藏的精魂。
目光上移,枝叶铺展如盖,浓荫匝地,筛下碎金般的阳光。枝叶深处,白色的影子静静栖落。魏老眯起眼,手搭凉棚:“看,白鹤筑的巢!”话音未落,一群白鹤,骤然振翅而起,羽翼划破晴空,排成一个大大的“人”字,翩然掠过青翠的山脊,飞向远方更深的蓝。鹤唳清越,久久地,回荡在坪上空。

魏老轻抚粗糙的树干,指着一处高耸的枯枝:“那年大旱,老天爷,不睁眼,硬是渴死了上头好些枝杈。”那枯枝,倔强地刺向青天,如凝固的闪电,无言诉说着挣扎。然而,树冠之下,更多的新枝勃发,绿叶层层叠叠,浓郁几乎滴下油来。枯荣共生,生死同在。这树,竟将时光的残酷与生命的韧性一同举向苍穹。
树荫浓密,罩住一片难得的清凉。树根盘踞的石条上,树下,经常散坐歇晌的村民。魏老低声解释:“在树下,开屋场会哩,村里大小事,老规矩了,都在这大树下议。”村支书站在中间,正高声说着什么,村民们或蹲或坐,凝神听着。一阵山风吹过,头顶古楠的万千叶片齐声响应,哗啦啦作响。那声响,清亮又浑厚,越过空旷的坪地,清晰地送入对面的人家。风摇枝叶,其声如语。这阅尽沧桑的老树,也在屏息凝听,以叶为耳,见证树下这方寸之地的公义与协商。

魏老弯腰,拾起地上一截枯干的小指粗的细枝,递给我:“莫看它枯了,这可是真资格的楠枝!”断裂处木质层紧密,在正午的阳光下,竟隐隐流淌一种内蕴的金质光泽,含蓄而贵重。言语间,他透着自豪:“村里人老话,树比人会记事。它能活到今天,是吸足这块地的力气。你看这坪,养人啊!”
顺着他目光望去,坪的坦荡,烟叶田碧浪翻滚,长势正好。新起的砖房,白墙黛瓦,点缀青山绿水,一派五谷丰盈的安稳气象。魏老絮叨着,村里走出去的人,当干部的,扛枪保国的,执掌教鞭的,都不少。他特意指了指远处山脚一栋老屋:“那家,还出过走过长征路的魏姓的老红军哩!”
立于这巨大的绿荫之下,仰观其冠,俯察其根,指尖触碰它嶙峋的肌肤。二百八十年风雨雷霆,它把根扎进银市坪的骨血,枝叶拂动银市坪的天空。它看过马蹄踏碎晨露,听过号角穿透硝烟,更在旱魃肆虐时咬紧大地的深处,以枯槁的枝臂,指向苍天,最终又让新绿覆盖了伤痕。树下,议事的乡音,烟叶田里翻涌的绿浪,新居上升起的炊烟,以及那些飞向远方的白鹤与游子……无不是它根脉所系的蓬勃生机。
风又起了,头顶的楠木枝叶再次发出宏大的声响,如涛如诉。它曾荫蔽过烽火岁月里的战士,如今又护佑着烟火人间里的生计与议事。树下,村支书的声音沉稳有力,正说到烟叶合作社的收成,说到如何用好这笔钱整修水利,灌溉更多的土地。村民们专注地点头,眼神里映着对好日子的期许。
此刻,阳光炽烈,古楠投下的浓荫,却如深潭,沉着清凉。它的根深植于沃土,枝干承接着天空。叶间的风声,传递着土地的脉动与人的心音。它不言不语,却以自身的存在,启示着一种深沉的力量:真正的繁茂,不在于始终青翠无虞,而在于历经雷劈斧斫、旱魃焦渴之后,依然能向下扎根,向上生长。在枯荣代谢中累积年轮,在静默中,荫庇一方水土的生息与共荣。
古楠树下的故事,如这大树一样,发芽。它被夜露滋润,被晨光点燃,在每一个日出月落间,生长成比年轮更厚重的希望。
责编:高丽文
一审:熊惠
二审:杨明
三审:陈桦
来源:桑植县融媒体中心

版权作品,未经授权严禁转载。经授权后,转载须注明来源、原标题、著作者名,不得变更核心内容。
!/ignore-error/1&pid=52030490 )
县政府月度例会丨梁高武:凝心聚力 真抓实干 以务实作风推动高质量发展
!/ignore-error/1&pid=51962010 )
曹飞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2025年第21次会议
!/ignore-error/1&pid=51962000 )
桑植县召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会
!/ignore-error/1&pid=51961655 )
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(扩大)2025年第8次集中学习举行
!/ignore-error/1&pid=51961990 )
桑植县民族团结进步标识LOGO、IP动漫卡通形象和主题歌盛大发布
!/ignore-error/1&pid=51933165 )
梁高武主持召开桑植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
!/ignore-error/1&pid=51813870 )
桑植县2025年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
!/ignore-error/1&pid=51745565 )
民族团结丨廖国豪来桑调研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工作
!/ignore-error/1 )
伴随着桑植的万物生长,打开脑洞,你还知道哪些桑植的“野生”汉字?#歌里画里桑植等你
!/ignore-error/1 )
千年赶一街,一街赶千年。芙蓉桥第十届“三月街”等你来相会!感受桑植民俗文化#民俗文化 #歌里画里桑植等你
!/ignore-error/1 )
是谁,送你来到大桑植 #桑植白茶 #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#乡村振兴 #歌里画里桑植等你
!/ignore-error/1 )
张家界桑植芙蓉街第十届“三月街”等你来#歌里画里桑植等你 #民俗文化
!/ignore-error/1 )
清明祭祀请牢记!桑植方言版森林防火口诀!#森林防火#全民参与
!/ignore-error/1 )
15分钟×4万学生=?桑植县用课间改革交出活力答案
!/ignore-error/1 )
冲刺高考 桑植一中学子开启逐梦新篇
!/ignore-error/1 )
记河口乡沙洲村支部书记陈仙娥的奉献之路

下载APP



